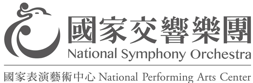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回顧原來是創新

撰文/焦元溥
進步,有很多種方法。
無論看法何其不同,最多人採取的,仍是藉由「研究過去以求未來方向」。華格納和布拉姆斯的立場與觀念相差很遠,但兩人都研究貝多芬,也從貝多芬得到前行的力量。功課做的最全面的,自然還是布拉姆斯,他1885年首演的第四號交響曲,就是最好的例子。全曲精練而充滿強大力量,既運用了調性之前的調式,也充分展現對奏鳴曲式與變奏曲式的深刻理解。尤其是第四樂章,大概只有布拉姆斯能有如此本領,把以低音為主題作變奏、古老的帕薩卡利亞舞曲,寫成石破天驚、澎湃激昂的交響樂。這個樂章為後輩帶來無限啟發,魏本的正式作品編號一,正是以它為藍本的《帕薩卡利亞舞曲》,在在告訴我們研究過去不是守舊,向經典學習也是創新。
借鏡過去,俄國的史特拉汶斯基則有另一番看法。寫出《火鳥》、《彼得洛西卡》《春之祭》,以俄羅斯主題聞名的他,1920年開始以新節奏、新織體與新和聲重新思考昔日音樂素材,跨入日後長達三十餘年的「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時期。「當時的評論家中,沒有一個人明白這點,因此他們對我就像對一個模仿者一樣地群起攻之。」史特拉汶斯基日後如此回看這段歷史,但他真正要做的,究竟是什麼?文學大師,也學習過作曲的米蘭・昆德拉,慧眼看出了這位作曲大師的內心:「現代一流作曲家和偉大小說家一樣(我指的是史特拉汶斯基還有荀貝格) ,都想將音樂史每一世紀納入作品,重新思考,重新融合傳統裡有價值的東西。[…]他們拒絕相信,音樂存在的理由完全只為宣洩個人的情緒(浪漫派音樂的觀點)。」藉由改寫與延伸,史特拉汶斯基「重新尋回過去音樂被遺忘的原理」,也和過去的音樂直接對話。
如此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這也是本屆音樂節的重要主題:我們看到太多現代或當代作曲家,或直接面對過去,或從過去獲得靈感,以此創作出他們的新樂曲。本屆音樂節駐團作曲家阿曼(Dieter Ammann, 1962-)的作品就是如此。在開幕音樂會要演出的鋼琴協奏曲《大觸技曲》,我們可以聽到「觸技曲」這個古老曲式如何化為概念,以及作曲家如何驅策鋼琴家使出渾身解數,展現排山倒海的精湛技藝。此曲先前已經由臺北市交首演,首演鋼琴家Andreas Haefliger也在BIS唱片公司留下錄音,兩者皆大獲好評。這次要在南台灣首度登場,相信也能令樂迷耳目一新,大呼過癮。
現代音樂中屬於新古典主義的作品,聽起來都很悅耳,但從二十世紀初至今,調性的瓦解與重組可說至為關鍵。「沒有調性」不表示不好聽,也不表示沒有調性元素,很可能只是作品「沒有調性中心」。閉幕音樂會要演出的理查・史特勞斯《最後四首歌》,其中的〈春天〉就是證明。歌曲開始於c小調,若照傳統調性觀念,要表現歌詞從冬天到春天的過程,結尾會是C大調,但史特勞斯顯然覺得這還不夠,於是樂曲結束在A大調。調性沒有回家,但我們也不覺得迷途,而是被作曲家帶往明媚春景。如果你對此曲不陌生也不害怕,那更沒有理由先入為主地害怕無調性音樂。同理,即使你不理解法國作曲巨擘梅湘的技法,聆聽他的《被遺忘的奉獻》,也能感受到這實是巨細靡遺的聲音色彩練習—誰叫他天賦異秉,具有能「看到聲音,聽見色彩」的聯覺(Synaesthesia)感官共生能力,也能以音符解析轉譯自己對聲音和色彩的感受。錄音沒有辦法真正捕捉他作品的現場效果,大家可要珍惜機會。
最後要說的,是作曲家的靈感可能來自你想像不到的地方。比方說布魯克納第六號交響曲,第一樂章開頭聽起來像是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配樂,但你繼續聽下去,就會發現它也很像《西城故事》—話說反了,應該是《西城故事》像它。這不是不可能:伯恩斯坦對布魯克納著墨不深,卻把他的第九號和第六號交響曲列入保留曲目。或許我們確實在這部百老匯音樂劇,聽到作曲家從布魯克納第六「借」來的靈感。參加本屆衛武營國際音樂節閉幕音樂會之前,不妨把《西城故事》再聽一次,說不定會有奇妙的意外收穫?
節目資訊
熱門標籤
推薦閱讀
在經典的縫隙中,窺見重生的現代光影與糾纏的鬼魂
很幸運能看到晃晃跨幅町的《海妲.蓋柏樂》整排,想起20年前也曾在北藝大演過這樣的經典,那時的海妲是謝盈萱,我則是布瑞克法官,當在排練場喚起熟悉的語句時,我內心拍手叫好,經典就是這樣,依然臉不紅氣不喘地跑在時代的每一刻,即使20年過去,那些句子像魔豆一樣在心裡持續成長,這正是1890 年問世的《海妲.蓋柏樂》,如今依然帶著令人窒息的現代性。

美聲.霹靂舞.奧林斯基
明星的成名之路,邁進21世紀後,有了另一條終南捷徑,那就是網路。網際之間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連古典樂壇也逃脫不了這種態勢,甚至更小眾的假聲男高音領域,近年出現首位征服Z世代的聲樂明星----來自波蘭的奧林斯基(Jakub Józef ORLIŃ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