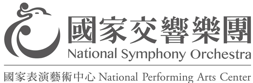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虛擬與現實,是誰走進了他的記憶裡?《留給未來的殘影》衛武營特別展演場

文|陳 昇(2020臺灣舞蹈平台書寫手)
「如果可以將火柴燃盡時間長度的記憶被記錄下來,你會選擇什麼呢?」
當穿著死神裝扮的人,手中燃起了一根火柴,並在伸手可及的位置對你說出這句話,可是看著他斗篷裡的臉卻暗黑到看不到輪廓時,整個驚懼、壓迫、緊張感油然而起。此場舞作透過VR和衛武營非典型空間的應用呈現出一場虛擬和真實的舞作。有別於一般參與舞作的觀賞和移動方式,舞作開始演出之前所有觀眾須戴起VR設備,並在指定片段後卸下設備直接接續舞者在非典型空間的舞蹈,進而產生一個看似虛擬但又得實際跟著移動觀賞的演出。
「誰又代表了誰?」透過舞者、玻璃帷幕和觀眾的關係,死神的這個問題看似在問著舞者,但也透過VR換位的方式同時讓觀眾接受這樣的提問,因此與其說我們是觀賞者但不如說我們也是真正的參與者,只是我們透過了虛擬影像的建置,以透視的方式來觀看與感受影像男子的不安與掙扎。只是在演出過程中觀眾的身份到底是什麼?到底誰是誰?誰又代表了誰?還是誰走進了誰的記憶裡?抑或是我們都是彼此的回憶?又或是我們都是彼此的主人(主意識)呢?
在真實舞蹈時,我們看著宛如遊魂般的舞者,認為他是被我們封入的記憶,可是站在他的角度從玻璃帷幕看到我們時,不更像我們才是真正被封入的回憶嗎?因為我們穿戴著奇怪的物品,眼睛還帶著黑色的眼罩,更像是個詭異的遊魂,畢竟舞者他還對著玻璃呵氣,而這更像是活著的象徵,所以到底誰才是誰珍貴的記憶?好像也說不準,但我知道的是現場演出中不斷吹過我們腳邊且滿滿發黃的紙應該就是片段的記憶,也因為上面沒有字,所以那些發黃的紙更像是我們該為此投射的回憶。
但在VR的影像中,有張發黃的紙倒是寫著「我們花了這麼久的時間長大,卻是為了離開」,這句話看起來好像是事實,畢竟所有人長大到最後都難逃一死,可是人最後的離開真的是成長的目標嗎?我們是為了這個目標才活著嗎?仔細一想好像也應該不是,因為人們在時間的流動中,傳承了某些重要的回憶、技藝、知識,也創造了許多溫暖且美的事情,而這樣的過程才更是成長的意義。
在這個作品中透過了VR呈像直接將劇場環境拉到了觀眾的眼前,更透過個人獨立式的參與方式讓劇院環境氛圍顯得更為真實,而這也有別於平常所參與舞作和戲劇演出,因為畢竟再怎樣的沉浸式也還是多人參與,而且縱然故事氛圍再讓人驚懼,也有著跟你在旁的觀眾一起,可是在這場作品中卻透VR過的呈現,直接將每個人的視覺參與獨立了起來,將演出的氛圍以更壓迫的方式親臨在觀眾身邊,進而強化作品傳達給觀眾的感受。另外,透過衛武營非典型劇場空間(樹冠露台和展覽空間)的應用,讓整場演出除了具備移動特性外,也讓樹冠帷幕玻璃形成了類似虛擬實境的擬態,我們透過了虛擬實境的裝置來參與虛擬的舞作,但在摘下裝置後,樹冠大廳的帷幕玻璃更像是大型的視聽裝置,也因此更錯亂了觀眾對於演出的角色與身分的真假,更讓人對死神和舞者留在牆上的句子產生回響,而這也是該場作品有趣的地方。
陳 昇
有著工學院的背景,卻喜歡看戲劇,擁有著海洋學院的對未知的好奇心,以及生農學院一步一腳印的樸實性,對環境教育有著一定的理想,目前在環保工程公司擔任水處理技術研發工程師,期盼工程的理性與藝術的感性可以相互結合。
閱讀更多:
推薦閱讀
小女孩的幻想雪花,臺灣的芭蕾夢—《遇見胡桃鉗的女孩》
《遇見胡桃鉗的女孩》,來自小女孩的幻想。幾年前,編舞家葉名樺還沒上國小的女兒,某日和聖誕老公公許下心願:「我希望家門口會下雪」。前一刻才信誓旦旦和女兒保證「什麼願望都能達成」,葉名樺不願打破承諾,於是在衛武營音樂廳舞台上,讓一群芭蕾舞者跳起出自《胡桃鉗》芭蕾舞劇的〈雪花〉,漫天撒下碎雪,一下就是三年。

美聲.霹靂舞.奧林斯基
明星的成名之路,邁進21世紀後,有了另一條終南捷徑,那就是網路。網際之間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連古典樂壇也逃脫不了這種態勢,甚至更小眾的假聲男高音領域,近年出現首位征服Z世代的聲樂明星----來自波蘭的奧林斯基(Jakub Józef ORLIŃ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