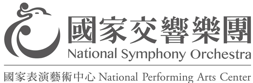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講座側寫︱當文字成舞-從文學、音樂及影像談《新娘妝》

時間:2019年6月1日
地點:衛武營演講廳
與談人:
- 《新娘妝》編舞|林美虹
- 《彩妝血祭》作家|李昂
- 《新娘妝》紀錄片導演|蘇哲賢
- 《新娘妝》作詞、協同作曲、演奏、演唱|游源鏗
- 《新娘妝》協同作曲、演奏、演唱|游麗玉
文字整理:尤博怡
6月1日,高雄豔陽依然熱情,刻意早到的我,看到林美虹老師已經在場內來回穿梭,謹慎、耐心地調整活動的執行細節;過程中,流露她的期待與緊張,畢竟,這是她第一次帶著《新娘妝》回到臺灣,回到這片孕育自己的土地。講座甫開始,在觀眾叨壤聲中,音樂家也是此次擔任《新娘妝》音樂編曲的游源鏗老師,以一首歌仔哭調《我叫一聲千金子》揭開序幕。這首曲子在《新娘妝》中,描述的是母親要送走孩子那幕的主要音樂,樂曲的情境感染力,瞬間就讓全場氣氛為之凝重哀肅。

講起與《新娘妝》的淵源,作為《彩妝血祭》作者的李昂老師娓娓道來。在一次參加國際書展的機會,意外與林美虹老師結緣;但其實讓兩人一拍即合的原因,是來自彼此對「人權」的關懷。《新娘妝》創作源起正是以「人」為出發點,著墨於關懷人性的普世價值;這也是為什麼,這件作品在2011年德國甫一推出,即入圍最高榮耀的「浮士德獎」,同時還在德奧地區巡演接近50場,感動上萬觀眾。李昂老師除了故事原創的身分之外,從《新娘妝》2011年的首演到2017年再次巡演,她都以粉絲的身分前往見證,也不遺餘力地與海外友人奔走;終於在今(2019)年因為實任文化部長鄭麗君的大力邀請之下,《新娘妝》終於踏上了回娘家的路了!
今年四月底,為了《新娘妝》首次在自己的家鄉演出,林美虹老師回臺親自參與素人演員徵選,這也是第一次她終於以《新娘妝》串起自己與臺灣這塊土地的連結。
從當時的一段訪談中,就已經可以深刻感受到,她嘗試在成長背景的那段空白記憶中,強迫自己正視且無懼地面對既已存在的歷史事件中的受難者,並試著從同理心昇華為憐憫及疼惜,在收納了受苦受難的椎心痛之後,如何以更巨大的正能量來反饋撫慰這些傷痕;藉由這樣的舞蹈與儀式,試圖撫平歷史的傷痕。但我想這並不是要我們遺忘歷史,而是以歷史文獻之外的的另一種方式,提醒自己、提醒社會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
而令人驚豔的另一部分,是為《新娘妝》譜曲獻聲的游源鏗、游麗玉老師,除了以古琴演奏、歌仔七字調演唱方式,將臺灣音樂元素極致地融合在舞作之中。說起與《新娘妝》的淵源,除了同為臺灣旅外藝術家,音樂創作能力備受肯定之外,我想很重要的一點,一樣是對「人」的那一份普世關懷。游源鏗老師憶起他在德國時,在前往劇院排練的路上,途中總會經過一戶人家,是當年納粹主義下的受難者家屬,他總會停下腳步,低聲說「我要為你們唱歌」,簡單的七個字,卻深切道盡對受難者家屬的不捨。就如林美虹老師一直強調「身為藝術創作者的責任,是感受社會的脈動,關懷普世人價的價值」。

而自2011年因為欣賞過《新娘妝》首演而興起用影像記錄的導演蘇哲賢回憶到:「比起紀錄《新娘妝》,我更有興趣的是紀錄林美虹老師。」這幾年來,蘇哲賢導演真切地記錄了《新娘妝》一路走來的淬鍊與成長。影像記錄是一種重製,在幾分鐘的影片分享中,將觀眾帶到《新娘妝》演出現場的震撼,舞者的旋轉、踢腿、時而緩行、偶而簌進;不管是群演或獨舞,都在蘇導演的鏡頭下,有節奏地步步進逼、慢慢竄進觀影者心底深處,將林美虹老師的意念,深刻地貫徹到舞蹈影像中。
講座接近尾聲,游源鏗、游麗玉老師以一首《落花》,再度用音樂洗滌聽眾的感知,此時的林美虹老師閉眼聆聽,彷彿透過音樂,把自己帶回了作品中;接著林美虹老師突然站起,誠心且堅定地向台下觀眾道謝,除了感謝觀眾到場參與,更提醒我們不能忘記現在享受的自由與人權,是多少前人的努力換來。對於原本帶著《新娘妝》回臺灣躊躇不決的她,在2017年的歐洲難民潮,讓她意識到同樣的傷痛並不只在遙遠的東方,一個「凝聚」的意念讓她決定,把《新娘妝》帶回台灣,透過《新娘妝》的演出、透過素人演員的參與,為長年禁錮在黑暗中的人,帶來一個光明的契機。
推薦閱讀
美聲.霹靂舞.奧林斯基
明星的成名之路,邁進21世紀後,有了另一條終南捷徑,那就是網路。網際之間無遠弗屆的影響力,連古典樂壇也逃脫不了這種態勢,甚至更小眾的假聲男高音領域,近年出現首位征服Z世代的聲樂明星----來自波蘭的奧林斯基(Jakub Józef ORLIŃSKI)。

廣播故鄉的歌聲,引你自在回家:【衛武營小時光】僻室House Peace《吳靜依—過溝》
來自「僻室House Peace」,穿梭在劇場裡、麥克風前的吳靜依,即將在春暖花開的三月,首度以樂團編制於衛武營舉辦專場《過溝》。在花季到來前,許瞳與人在東京出差中的靜依跨海連線,聊聊此次專場的企劃,以及新年度對於音樂、創作與家鄉的想像。 (*內文中靜依簡稱「靜」、許瞳簡稱「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