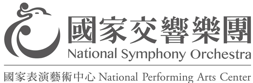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簡文彬眼中的編舞家 馬汀.薛雷夫 與《馬勒第七號》

文/ 盧家珍
一位是從1996 年起擔任德國萊茵歌劇院駐院指揮長達22 年,現任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藝術總監的簡文彬;一位是改造德國萊茵芭蕾舞團,當代最成功編舞家之一的馬汀.薛雷夫,今年兩人再度攜手,共同演繹鮮少被演奏的馬勒第七號交響曲所編創的現代芭蕾作品《馬勒第七號》。在演出前,我們透過簡文彬,來認識這位頻頻獲獎、為芭蕾找到當代獨特語彙的編舞家。對於臺灣觀眾來說,芭蕾和音樂家馬勒是十分新鮮的組合。雖然改編馬勒作品為芭蕾舞作品,薛雷夫並不是第一位,但看在老搭檔簡文彬的眼裡,他卻希望觀眾能夠用心感受,看看薛雷夫是如何以舞蹈與社會連結,展現靈魂深處的關懷。
音樂直覺感受力強大的編舞家
「馬汀.薛雷夫與林懷民老師,是我遇過音樂直覺感受力最強大的兩位編舞家。」簡文彬說,他們都強調自己看不懂五線譜,但是當他們聽到音樂,就能快速地抓到脈絡和發展,甚至還能預測下一個音是什麼,「簡直是天才!」2002 年,簡文彬和國家交響樂團演出《托斯卡》,邀請林懷民擔任導演,第一次見識他在音樂情緒和張力的超級感受力;2012 年,簡文彬在萊茵芭蕾舞團又在薛雷夫身上看到相似的情景,他們一起合作改編了布拉姆斯、莫札特、盧托斯瓦夫斯基,以及馬勒的古典音樂作品,每次選擇要使用哪個演出版本時,薛雷夫對樂團的詮釋總有很強的直覺,讓音樂與肢體能夠切合得天衣無縫。
簡文彬認為,薛雷夫翻轉了萊茵芭蕾舞團的形象,不使用傳統命題式的舞劇架構,單純使用音樂和舞蹈來表現他的主張。在他的帶領下,古典芭蕾裡的所有階級也被打破,舞團沒有首席,也無當家花旦,在他的作品中沒有很明確的男主角、女主角,每位舞者在每個段落都是必要的存在,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發揮機會。「他編舞的態度十分開放,認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所以他從不要求大家一定要跳得一般高,或是動作要整齊劃一,但必須對音樂要有感受和反應,若只死記動作,他可是會罵人的!」簡文彬笑道。
在舞作中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在簡文彬眼中,薛雷夫不僅和林懷民都屬於「直覺敏銳」的編舞家,他們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大環境的關懷。林懷民關注歷史和社會脈動,薛雷夫則關心地球和歐洲動態,而《馬勒第七號》就是一齣探討族群疏離感的作品。薛雷夫以馬勒第七號交響曲的五個樂章,編成一個多小時的舞作,把舞台化為整個世界的縮影,舞者時而穿著靴子、足尖鞋或芭蕾舞鞋,時而赤足,他一手打造的世界如夢似幻,不同的交錯場景看似合乎邏輯,卻又相互衝突。在馬勒交響曲的恢弘結構中,以肢體盡現人生的艱難。
馬勒曾說:「我算是三種層面上的無家可歸:一是作為奧地利人中的波西米亞人,二為德國人中的奧地利人,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我像極了一位永恆的外來入侵者,到頭來也無處可去。」簡文彬認為,馬勒本身就是爭議性的人物,在哪裡都覺得自己是異鄉人,薛雷夫選擇了馬勒的作品來訴說族群問題,也是恰如其分。
簡文彬眼中的馬勒加芭蕾
那麼,身為指揮的簡文彬,又是從什麼角度來看馬勒第七號交響曲和芭蕾的組合呢?簡文彬笑說,馬勒是作曲家,又擔任過指揮和劇院總監,他的作品「非常知道指揮要什麼」,大家都很愛指揮馬勒,對樂團而言也是一種樂器極限的挑戰,每每演出後都能達到一定的爽度(成就感)。不過,在馬勒所有的交響曲中,第七號交響曲卻是較少露面的作品。「馬勒有『終樂章作曲家』之稱,意謂所有菁華集中在最後一個樂章。」簡文彬說,但是第七號交響曲卻一反常態,把菁華都集中在第一樂章,呈現「頭重腳輕」的狀態,因此很多指揮不敢輕易處理這首交響曲,怕在最後樂章轉不回來。然而加入了舞蹈後,簡文彬認為剛好讓樂曲有了平衡的契機,當最後的音樂分量變得輕鬆時,舞台上的芭蕾適度補足了情緒上的空白,提供了一種新的欣賞角度;而他也透過合作過程有了重新思考的機會,並從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讓將來單獨演出《馬勒第七號》交響曲時,能展現全新氣象。
編舞家與指揮的磨合
相較於國內舞蹈演出多半使用預錄的音樂,歐洲則習慣由樂團現場伴奏。對音樂一向有高標準要求的薛雷夫,對指揮也很挑。簡文彬雖然與他合作多年,兩人在工作上難免有磨合過程,有時基於立場不同,還會出現「打槍」的畫面。「通常我們合作的SOP 就是——挑選錄音版本→看舞蹈彩排→討論音樂如何搭配→樂團排練→合演。」簡文彬以選定音樂版本為例,通常他會從自己的音樂經驗出發,推薦一些不錯的版本,但他所蒐集的大多是在1960 年代之前的錄音,1970 年後的不到1/5,偏偏這些版本經常被薛雷夫全盤推翻,還打槍說:「我的舞蹈情緒性很強的,音響很重要,這些單聲道的錄音,現在聽起來沒辦法滿足我的需求。」
而針對「情緒性」要求,簡文彬也有話要說。正因為薛雷夫對音樂的敏銳度驚人,他總是能聽到錄音中的細微音響,例如三角鐵清脆敲擊聲,或是低音提琴的撥奏聲,這時他會感動的說:「對!我就是要這個聲音,剛好搭配舞者的情緒和動作。」此時,臉上「三條線」的簡文彬必須花力氣告訴他,三角鐵和低音提琴到了現場演出時,就只有「叮」和「咚」的微弱瞬間,和喇叭播放出來的音響是完全不一樣的。「當然,我還是會尊重他的想法,看看樂團有何方式可以透過演奏來放大情緒的部分,例如用鐵琴補足三角鐵的不足。」簡文彬說,和樂團排練前,他會先去舞團看看,了解舞劇的張力在哪裡?樂團可以怎麼協助舞者們發揮?什麼地方可以多留一點空間?都可以做一些調整,若是破壞太多原本的音樂架構,他才會和薛雷夫重新討論。
在簡文彬的觀察中,薛雷夫創作時,總是在尋找一種能讓他浸淫其中,並埋首工作的音樂。他不需要具體的敘事結構,而將重心放在當代人們生活中的奮鬥上。這樣獨樹一格的特色,讓簡文彬每次指揮時都有一種新鮮感。「有的人創作是在探索自己,有的人創作是為了表達主張,薛雷夫很明顯是後者。」簡文彬建議大家在觀賞時,不要有太大的包袱,也不必做太多研究,不妨打開自己的感官,看看薛雷夫是如何運用舞蹈傳達他的想法,或許在音樂的碰撞之下,將會有更多的感動。
本篇刊載於臺中國家歌劇院《大劇報NTT Post》No.16,2019年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