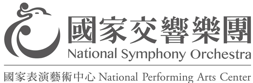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舞台下的影舞者─專訪攝影師金成財

我因此對於他熱切的神情與滔滔不絕、手勢繁多的積極姿態感到有些意外。一位善於等待光、等待風、等待緩步而行的舞者、等待十年磨一劍的編舞家的攝影者,不是應該沉默少言、靜如磐石嗎?我正這麼想的時候,他有點困擾地撫過了滲著汗的前額,些許凌亂的長髮被隨意束在腦後,他甚至帶點侷促地提起拍攝無垢的困難處:「哎呀,就是那個快門太大聲啦!」
文字│張慧慧
追尋霧中風景
生於南投信義鄉,一半客家,一半布農族血統,從小就是山裡來,河裡去的野孩子,金成財十二歲第一次才見到海,二十歲時到台北,隔年首屆金馬影展舉辦,那是1990年,他一頭撞進海那頭更寬廣無際的電影方格世界裡,從此迷上透過鏡頭看世界。
牡羊座風風火火的性格拿起攝影機,衝鋒陷陣不在話下,處在90年代風起雲湧的台灣,目光自然垂落在週身快速轉變的社會現實,以松山機場飛機起降的「安全降落」系列作品,獲1995年台北國際攝影節新人獎;隔年,他最為人所知的「稻草人」系列獲該年度攝影首獎。
「《霧中風景》是我的啟蒙,這部電影裡有一幅關鍵的畫面,是片中小男孩的一張照片,他透過這張照片尋找他媽媽。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幅畫面,我的是我家的一片水田。」他頓了頓,在那幾秒中,那棵1988年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所凝視的霧中的樹,跟金成財在南投家鄉中的稻田就重疊了,「我伯父在那裡造了一個稻草人,河谷裡的稻草人。田土旁的河谷,吊橋,光撒下,那條和我媽總是一起走的,長長的路,山谷後面是下了雪的玉山,稻草人的衣服被風吹起,揚得好高,還有那條河,像那條《觀》裡也出現過的河流,我的童年都是從這幅畫面開始。」
慢過時間的舞者
《觀》是無垢舞蹈劇場創辦人暨藝術總監林麗珍天地人三部曲的終章,首演於2009年。鷹族之爭,白鳥之死,天與地,神性與慾望……林麗珍透過傳說故事建構廣袤的宇宙觀,「慢」是形,「緩」是心,在林麗珍的世界裡,時間之流濃稠凝滯地像在外太空,有香港的觀眾在一次演出結束後,半開玩笑半真心地問:「林老師,您是外星人嗎?」
「說實話,我也曾經看到睡著啊。」回答如何看待這位編舞家最著名的「慢」,金成財誠實地笑了。他說,他有時會在演出時分心數離場的觀眾,「五個走了,六個走了,七個,十個……我總在心裡大喊,再等一下啊,再等十分鐘,好看得不得了啊,怎麼就這樣走了!太可惜了!」「看她的作品像在修行,因為她慢,所以讓你有更充足的時間去體驗、去看。」
舞者們甚至慢過自然,緩過時間。幸虧紀實報導出身的金成財早已習慣揮霍大把時間守候拍攝對象,一張舞者在陽明山七星池緩步而行的照片,他拍攝舞者的水中倒影清晰可見微風吹過的水紋,時間彷彿正從舞者身上行過。「這必須用很長的時間去觀照,時間是重點,我想要抓住時間,後來發現根本抓不住,但你做一個空間你就抓得住時間了,林老師非常會造出這種空間,不去迎合任何人,用簡單的結界,狀態的能量去創造一個世界,簡單卻純粹,歡迎任何人進來,放進自己。」
金成財言談間必尊稱林麗珍為師,這對相差十九歲的「師徒」相識地很早,1991年兩廳院的「原住民樂舞系列──布農篇」林麗珍是編舞家,甫畢業的金成財擔任志工。但兩人直自2002年一次採訪才開始合作,林麗珍絕少與他談論劇照,只一次金成財送了一楨照片給她時,她沉吟良久才說:「這張很好,但姿勢沒有到位。」編舞家看照片注視的是舞者身體的形,攝影師凝視的則是空間與光。
「一開始試著想去理解作品,想去懂,但到後來,你已經可以閉著眼睛去看到另一個作品。」那作品關乎觀者自己,如鏡面反射自身,他說:「老師的作品像詩,純淨,撕裂你,她造出一個空間,讓你自由地帶入自己的觀點、情緒。」
金成財以攝影者,以單純觀者的身分,毫無罣礙地把自己嵌入了林麗珍空間中的留白。「到後來,我在劇院裡閉起眼睛只聽音樂,也可以清楚地看見這個作品,知道舞者們走到了哪裡,擺出什麼樣姿態……」有次在俄羅斯演出的後台,他闔上眼卻看到《觀》的每個細節,想起父親過世後與家人的拉鋸,想起故鄉的河、稻草人、河谷兩側吊橋上的天光……原本耿耿於懷的不諒解因此得到釋放。
攝影者的「殺」與「不殺」
翻看厚厚一疊篩選中即將付梓的《觀》攝影集照片,一系列在陽明山七星池、南投溪頭衫林溪、苗栗天然谷、台東衫林海岸、雲林萬年峽谷等地拍攝的照片令人驚艷,人在自然中顯得脆弱又渺小。早已習慣在舞台上承受千百雙目光,對自我極度自覺的舞者們見著照片好驚訝:「這是我嗎?」他們問。
金成財細細解釋每一張的構圖,與拍攝當下的情境,不只一次提到快門聲的干擾,「太安靜了。明璟跳的白鳥掉淚時,我每次都可以聽到淚珠掉落的聲音。」因此,他按快門近乎守禮般克制。攝影者盤絲錯節跟隨表演移動的思想,讓按快門不是反射性的行動,而是縝密計算的結果。他說:「無垢拍的是心,不是形式。拍到後來,快門聲與舞者的呼吸是一樣的。很多人說:『啊你就快門一直按一直按就好了。』快的動作可以交給快門,但無垢不行。事情沒這麼簡單。」
有舞者說,「我聽得出財哥的快門!」無垢的舞台視覺太美了,美之物特別容易勾起攝影者的狩獵本能,在彩排記者會一片槍擊般攝影快門聲中,與環境融為一體的舞者們五感如獸,居然辨別得出金成財的快門聲。「每次拍他們,我都覺得快門聲太大了,很煩呀!後來,按快門我也有自己的節奏,就像是台下的舞者,跟他們一起移動。」
一張在景美人權園區彩排時,微風捲起白綢裹住緩慢墜地的白鳥吳明璟,脆弱、沉靜,彷彿能讓人感覺細微的呼吸。這張偏離舞台主視角的照片,是在舞台工作人員才可見的角度拍下的。就這一張,金城財說,那天就值得了。拍下那張照片的隔幾天,林麗珍突然偏過頭提起那陣排練場上神來一筆的微風:「阿財,那陣風、那道光好美呀。那包住明璟的樣子。你有沒有看到?」去頭去尾地沒有太多的說明,他卻心領神會,忍不住笑了,「有啊,老師,我拍下來了!」
頻率相近的編舞家與攝影師,讓舞蹈持續進行的瞬間得以駐留,抵達無言之境。
或許,沒有任何藝術形式,是比舞蹈更難趨近語言的了。言語性的分析,對於意識停留在表面的作品或許有效,但對於將問題藏在意識深處的創作者而言,以語言強求也只是隔空搔癢。
金成財分析林麗珍的作品高明之處在於「那些沒有說出來的部分」。他以侯孝賢《聶隱娘》相比,以片中隱娘助父親都虞侯聶鋒躲避暗殺之夜,鏡頭對準寒愴木屋裡的火、疲憊睡去的聶鋒,而夜驚的飛鳥聲,暗夜中的的關門聲都在畫面之外,卻讓觀者心知肚明隱娘在暗夜中護衛父親,刺客來襲等意在言外的情節,他說:「他們兩人的意境是相同的,這是用生命累積出的厚度與修為。」
話又說回來,隱娘的殺與不殺,編舞家、導演的說與不說,攝影者的快門按與不按,皆存乎心。而面對安靜如斯的舞台,在攝影普及的暴力「喀擦」殺伐聲中,謹守快門分際的金成財,也可以說是仁心充滿的「刺客」了。
熱門標籤
推薦閱讀
輪轉千迴,只為再見伊人一面:無垢舞蹈劇場《潮》
看林麗珍的舞,就像看極慢速動作的電影。4K高畫質的影像、以每秒120幀畫面的速率,在眼前安靜流淌而過。每一幀畫面都那樣細膩而絕美。 而那樣的絕美,卻是她帶著舞者,以時間慢燉提煉的生命精華。作品中以「緩行」建構的獨特身體語彙,充滿豐富的情感細節、簡約雕琢的視覺意象,像一場莊嚴的儀式。進劇場看她的作品,不只看舞,而是走進生命的殿堂,與舞者共同完成一場身心沉浸的祭典。

愛我就吻我,不要問我:《羅恩格林》的幻想與追尋
1859年,16歲的巴伐利亞王子路德維希二世,第一次在劇院聽見華格納的《羅恩格林》。那天之後,他彷彿被什麼召喚,從此活在自己的幻想裡。三年後他即位,沒有變成一位深知民疾苦的君主,而是成了一位愛玩cosplay的白日夢冒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