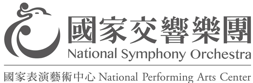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若看完《火鳥‧春之祭》,史特拉汶斯基也會發限動

©Susanne Reichardt
文|魏琬容 OISTAT國際劇場組織執行長
談起史特拉汶斯基,大多數人會想到《春之祭》,相傳《春之祭》首次演出時,觀眾詫異不已,震驚轉為憤怒,甚至演變為叫囂。原因無他,《春之祭》實在太怪了,不協調的音樂、怪異的「芭蕾」舞,讓1913年的觀眾深感被冒犯。
其實,時間再往前推到1910年,史特拉汶斯基的第一部芭蕾《火鳥》可是大受好評,《火鳥》讓才28歲的史特拉汶斯基一戰成名,打響名號,沒想到《春之祭》爭議卻這麼大。短短數年間,史特拉汶斯基推出兩部震撼作品,如果一百年前有instagram的話,我可以想像當時的評論人發限動「哎呀這個傢伙啊,作品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呢」(配上表情微妙的自拍圖 )
等一下,真的嗎?
一百多年後回顧,《火鳥》跟《春之祭》都是識別度極高的作品,也難怪編舞家伊凡‧沛瑞茲(Iván PÉREZ)想要一口氣編兩個(推測是一種「一個不夠,我要兩個」的心情)在原始版本中,男主角抓住了火鳥,火鳥急於掙脫時,落下了一支羽毛,火鳥告訴他「遇上危險時拿出羽毛,就可以召喚我」,而《春之祭》的故事更為直接—人們選中一名女性獻祭,被選中的女性被迫狂舞至死。
兩部作品都是男性中心思維,被抓住的都是誘人的他者(鳥類、或是女性),而且,鳥類比女性幸運一些。火鳥用一根羽毛暫且換得自由,而 《春之祭》中的女性更慘,不僅沒得選擇,連命都沒了。
在《火鳥‧春之祭》中,編舞家做了有趣的調動,《春之祭》中被獻祭的改為男性。雖然我已預先知道被獻祭者是男性,但是,當我看舞蹈片段時,卻彷彿在看《魷魚遊戲》—因為我完全猜不到誰會被犧牲,誰會活到最後,看起來每個都有機會(真心緊張)。而我會聯想到《魷魚遊戲》是有原因的,因為,火鳥一上來先玩起「一二三,木頭人」(而且是用中文),接下來,舞者們時玩起鬼抓人,時而捉對廝殺,編舞家藉由「遊戲」來貫穿《火鳥》與《春之祭》,探討規則的建立與打破。傳統上,被獻祭的人總是被剝去衣物,而這版反其道而行,被選中獻祭的人被一層又一層的衣服蓋住。舞台上有滿地散落的色彩鮮艷的時裝,直可比蔡依林最新MV的色調。然而,色彩斑斕不代表舞作甜美,相反的,編舞家精準捕捉那股身不由己、不由自主狂舞的感覺。既維持原版精神而又注入新詮釋,這就是伊凡‧沛瑞茲版本《火鳥‧春之祭》的特色。2024年距離《火鳥》和《春之祭》首演已經超過一百年了,我想,喜愛突破自我的史特拉汶斯基,如果見到他的兩個作品被如此串接,應該也會發個限動說「雖然沒想到,但很不錯喔。」
節目資訊
5/4(六)14:30、5/5(日)14:30
熱門標籤
推薦閱讀
我們的舞蹈,我們的歷史,從你開始! 「臺灣舞蹈記憶地圖」計畫啟動座談會側記 ──研究為經、推廣為緯,與時間賽跑!
超過百位在不同年代為臺灣舞蹈奉獻的專家、學者,連同關注舞蹈的人士,在2025年12月7日齊聚一堂,共同參與「臺灣舞蹈記憶地圖」計畫啟動儀式暨為期一天的座談會。眾人的熱切投入,使風和日麗的衛武營成為建構臺灣舞蹈史的「應許之地」,也讓這個為期四年的研究與推廣計畫,有了一個備受祝福的開始。

當京劇想像遇見法國幻象 ── 國光劇團《公主與她的魔法扇》
知名京劇《借扇》的故事情節取材自小說《西遊記》,講述孫悟空為了借用芭蕉扇煽熄火燄山的烈焰,因而與鐵扇公主大打出手,最後巧妙化身蒼蠅飛進公主腹中大鬧一番,終於取得法力強大的芭蕉扇,師徒一行也得以平安越過火燄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