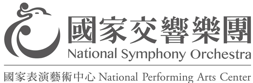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天才蠢蛋》,既原始又混種的邊緣身體

文|周伶芝
脫離傳統馬戲團的帳篷、不再展現馴獸奇觀,表現對動物權的意識,也為馬戲的藝術性請命,1970年代在歐洲開始發展的當代馬戲,從人的技藝追問人的本質。做為舞台上唯一的動物,人類的馬戲最終是要馴服自己的慾望,還是要釋放內在深處的動物性?多年來,有不少當代馬戲創作者以互異手法探討這一命題,各有不同詮釋,也為當代馬戲累積出豐富的身體圖景和敘事。
斯瓦爾巴德馬戲是由四位來自不同國家、身懷絕技的年輕創作者所組成,2014年一起從藝術大學畢業後,便留在斯德哥爾摩成團。期間曾與Animal Religion這一不按牌理出牌的馬戲團體合作,此團體喜歡狂野沒有邏輯的風格,在特定場域如動物農莊為演出場所,一群演員被追著或追著堆草機狂奔,意圖要解放人和動物之間的界線。經過如此作品演出的洗鍊,四位夥伴再度聚首同台創作演出自家創團作《天才蠢蛋》,便可見其思考之延伸。他們認為每個人的內心同時並存天才與蠢蛋,也就是理智和本能的衝突,然而,這條界線真的如此分明、如此好判斷拿捏嗎?況且,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和游移的界線究竟是由什麼來決定?而本能與智性兩者間真有如此大的分野?我們會不會同時是天才也是蠢蛋,我們同時在劃分又在自我推翻?
從人性的模糊、曖昧開始挖掘,《天才蠢蛋》逐步帶我們看到生命的荒誕不經,存在的痛與歡快。場上堆著超市推車、幾袋舊貨,豎立的爬桿和懸掛的吊燈,舞台予人一種嬉皮或是遊牧民族的氛圍。他們玩笑式的嬉鬧或帶著挑釁的粗野表演裡,彷彿無政府狀態。一開始,身體的每個部位各有各的主張,得靠某種意志、自身的戰爭去協調彼此,馬戲在說著屬於蠻族初生的身體語彙。褪去毛皮外衣後,又進入關於水的寓言,無水可即時解渴,人與人之間是否會因此做出傻事,彼此的身體成為挑戰和征服的競技場,喝水成為儀式。幽默是這齣戲的基底,以節奏和身體的變化挑戰來尋找人的象徵,他們在角力中演繹暴力和死亡衝動,在民謠的吟唱裡換裝,演繹組裝時代的自我混種。
於是這群遊戲的人,像是在廢棄社會裡的流浪者,以馬戲同時表現人的機械性和動物性,身體的原始動能可以創造超現實的安靜和詭異,探討「邊緣」所激發出的抵抗和創造。這可能是天才也是蠢蛋、兩者相互交錯的時刻,可以辨識出我們內在神聖的愚蠢和狂歡的天才憂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