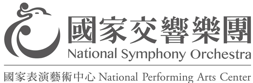衛武營本事
印尼新銳編舞家里安多對於「恍惚狀態」的解讀及其創作歷程

訪問者|海莉.米那提
曾與英國阿喀郎・汗舞團巡迴演出,並在班加羅爾、東京等各城市創作的里安多,將自己的創作理念深根於萬由馬士文化。里安多的作品《方寸之間》探索肉身以及在爪哇島中部的家鄉萬由馬士,其中參雜了gending(甘美朗的作曲配置)以及特魯圖耳(歌樂)元素。
肢體語言:誰控制了什麼?
《方寸之間》如何創作生成?
這件作品的靈感誕生於2013年班加羅爾的阿塔卡拉里藝術中心的兩年駐村期間。那段時間,我觀察當地人的習性以及印度的各種社會樣貌。
我對當地人的肢體語言特別感興趣,例如,交談時頭與雙手的擺動。我開始研究當地的古典舞蹈,像是婆羅多舞、卡薩克舞,以及奧迪西舞。我發現這些古典舞蹈中許多肢體動作與當地人日常說話時的肢體動作有許多相同之處。
其中有幾個動作特別吸引我的目光,為什麼當地人說話時頭與雙手會擺出這些特殊線條與弧度動作呢?他們說話時大腦真的意識到肢體的這些行為嗎?
這使我反思,身為一名舞者,我的肢體動作一樣深根傳統文化,例如凌雅舞蹈(一種爪哇地區的女性舞蹈,不過舞者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當地人相信舞者在舞動中會被祖靈附身)或者庫達可潘 (或稱「入神舞蹈」,這種舞蹈過程會有巫師唸誦特定心法,使舞者(大多是男性)進入一種精神恍惚的狀態,並表現出類似瘋馬的動作,甚至出現各種不可思議的舉動,像是啃食一整顆椰子或者咀嚼碎玻璃。這時,舞者會發出奇異的聲響或者出現類似動物的行為)。我思索著,身體進入這些恍惚狀態時,是否仍受到大腦控制?我決定要以這個「無腦身軀」的概念,也就是以一個恍惚狀態的軀體為核心來創作。
你如何開展這個發想?
那次駐村結束後,我嘗試以較短的作品闡釋「無腦身軀」的理念。當時我有部分時間在日本創作,那檔作品由鈴木愛理演出,音樂的部分則由坂本龍一創作,於西蘇門答臘的巴東Bagalanggang表演藝術節演出,那也是我與賈菈相識的地方。
我與賈菈約好在2014年的印尼舞蹈節(IDF)再次碰面。2014年IDF中,許多國際策劃人前來觀賞我的作品,我與他們分享「無腦軀體」的創作概念,也表示希望進一步發展這部作品,賈菈當下就答應擔任我的製作人。
2014年IDF會場上,達姆施塔特州立劇院的布魯諾・亨德里克以及來自比利時安特衛普(德辛格)藝術中心的卡林・梅根克(Karlin Megank)雙雙邀請我前往達姆施塔特與安特衛普駐村,並將駐村納為創作的一環,於2016年演出該作品。
鼓樂與肢體律動
那次駐村是在何時?過程如何?
2015年10月我有機會前往達姆施塔特駐村兩週。大約五個月後,我將這個創作構想帶到印尼加里曼丹的垃庄藝術節(Lanjong Festival)。
那次駐村期間,我把重心放在聲音設計,我非常想要納入身體在恍惚狀態中所發出的聲響,例如心跳聲、腹腔聲、呼吸聲等。布魯諾介紹我認識挪威籍旅德電子作曲家吉斯勒・馬丁・梅耶(Gisle Martens Meyer),他幫我錄製了這些發自身體的聲音。
除此之外,吉斯勒還從醫療管道找到了其他的錄音檔,於是我們開始密切合作。雖然我們最終無法採集身體在恍惚狀態時所發出的聲響,我們還是嘗試了這項實驗手法。另外,我們還前往墓園,設法理解這類場所的聲域狀態。
編舞的部分呢?
這件作品將重心放在萬由馬士地區的特魯圖耳或聽邦(傳統古典爪哇的旋律與歌詞)。 通常,特魯圖耳所描繪的是不同的旅程,因此,我用其表示身體的不同經歷,就像街頭藝術家一樣。
查詢資料的過程中,我還回到萬由馬士籌劃一場社區型演出。我邀請達爾文藝術節 的安德魯・羅斯以及電影製片人加林・努格羅前來觀賞。我在該次演出與SMKI藝術高中的學弟、傳統長筒鼓鼓手倫波可・賽圖雅吉(Rumpoko Setyoaji)一同即興演出。
後來我發現自己的身體無法與電子音樂產生共鳴,因此還是恢復使用傳統音樂,我意識到我對長筒鼓情有獨鍾。在萬由馬士傳統音樂中, 長筒鼓樂手與舞者簡直就像夫妻一樣,彼此密不可分。後來,安德魯同意於2016年呈現該作品,加林則以戲劇顧問的身分參與製作。
接著,我在2016年初前往安特衛普德辛格駐村兩週。我在那次駐村期間精煉了這件作品的構想,並且與倫波可密切合作。當時我給了倫波可一些意見,但他似乎難以超越傳統巴肯的風格進行即興創作。後來我開始著手舞蹈架構,我想起精靈(祖靈)如何透過凌雅舞蹈進入我的身體,以及那些我在年幼時聽過的說話聲。在那不久之前,我曾在返鄉期間的睡夢中聽到重複的鼓樂節奏,那段節奏不斷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因此成為作品的一部份。我在安特衛普進行的就是這部分的創作。
以恍惚的肢體作為媒介
什麼時候從「無腦身軀」演變成《方寸之間》的呢?
我在安特衛普時,呈現作品給較小的觀眾群,希望藉此得到更多回饋。就在那期間,我想到了「方寸之間」這個詞,覺得這個標題似乎比「無腦身驅」更加合適。
其實早在阿塔卡拉里駐村期間,就有許多人質疑、批評「無腦身軀」這個題目。當時周遭的藝術家與策展人都對這個主題有疑慮,畢竟這個題目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醫療上的腦死狀態。一開始我堅持使用這個題目,但在安特衛普期間,我開始思考身心障礙者的處境,以及他們如何需要透過特殊工具或媒介來彌補軀體上的缺乏,才得以表達自我。這讓我意識到處於恍惚狀態的身軀其實也是一種媒介。
回到印尼期間,我邀請以前在萬由馬士的同學卡瓦蒂演唱作品中的特魯圖耳,原定計畫的長筒鼓鼓手因故無法演出時,卡瓦蒂自願表示可以同時演奏長筒鼓,畢竟那是他非常熟悉的領域。
《方寸之間》於2016年8月在達爾文藝術節首演,共有六場演出,同年10月還前往達姆施塔特巡迴了兩天,同月也在德辛格演出了兩天。《方寸之間》也在2017年6月於雅加達薩里哈拉演出。些微修改作曲之後,《方寸之間》在2017年前往歐羅巴利亞藝術節巡迴(印尼是2017年歐羅巴利亞藝術節的重點國家)。
創新的協作與聲音創作
即將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演出的《方寸之間》又是什麼樣子呢?
這個版本是由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雪梨表演空間,以及台灣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共同製作。我非常希望可以重新編排聲音的部分,畢竟這件作品是由(身體的)聲音發想而來的。
過去參與阿喀郎・汗舞團的舞蹈演出時,我對他們的聲音設計印象深刻,尤其是音效與音響的部分,以及這些元素所營造的整體效果,我希望以同樣的方式呈現卡瓦蒂的歌聲。這個夏天我在高雄十天的駐村期間,聲響效果是我所著重的部分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也改變了呢?
這次我邀請了鄧富權(新加坡)以及森永泰弘(日本)擔任戲劇顧問與聲音設計,兩位對於我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富權提醒我,自從我們在2008年由雅加達藝術發展局舉辦的戲劇顧問工作坊上相識,過去十年期間他持續關注我的創作。我在2013年擔任北村明子的舞者時認識了森永泰弘。此外,加林仍然在許多基本面上給予意見。我覺得跟兩位戲劇顧問合作是很棒的經驗,兩位各有千秋、相輔相乘。
*本文章為《方寸之間》2018年於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演出時之委託創作,並首次刊登於www.esplanade.com/learn,如欲轉載請取得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同意。
*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是《方寸之間》共同委託創作者之一。